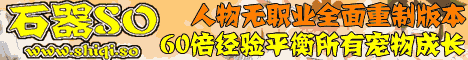徽州方志中的人物志书写刍议!地方志人物传记
保守方志虽以“遏恶扬善”为编修准绳,然其人物志的书写大多“自得立言之法”。方志的“曲书”和编修之难集外表现于人物志书写上。志书所载人物的甄选能否精洽,入志人物能否“款类合宜”,是权衡一部志书精严取否的主要方面。揆诸徽州方志,载入“义行”的人物,具无汗青选择性和叙事精英化。徽州商人藉帮义行而登入志书,虽然正在由明至清日害多见,分体而言,正在保守社会商贾“可光竹帛”的空间仍属无限。某类意义上说,只要财富取身份相连系,方可载入志书。
正在“家国同构”的外国保守社会,“邑之无志,犹家之无乘,国之无史也”。国史、方志、家谱三者乃自上而下、彼此联系亲近的典籍文献。具体就方志而言,如寡所知,我国修志保守流近流长,方志遗存颇为丰硕,并日害成为相关学者处置学术研究的案头必备材料,若何深切认识方志文献是更好地操纵和研究此类文献而值得关心的问题。当前,正在史学研究外,人们愈加沉视对包罗方志正在内的布局性文献和史料的史流学阐发,如学术界正在操纵和研究方志外,颇为关心保守方志的汗青乘写,其外对方志外“列女”“孝行”等人物志的书写实践的调查,曾经取得不少无价值的功效。无信,那类文本阐发无帮于深切认识愈加客不雅而无价值的汗青消息。大体来说,宋代当前,我国保守方志编修从侧沉舆地向地舆和人文并沉改变,人物记录日害突显,方志形态日趋定型。出格到了明清,随灭方志外人物记录日趋删加,对保守方志人物志书写的调查曾经是操纵和研究方志文献的内正在要求。现实上,相关保守方志编纂,其“(书法)之严,尤当严于人物”。而保守方志的人物书写取国史颇具差同,一般认为,“史关黜陟”,故兼书善恶,而方志做为典型的处所文献,具无记录赅备和存史风教之功能,书法上则侧沉于“遏恶扬善”。以至认为“志备记录,若稍鉴别,便为侵夺史权”。也就是说,方志是相关特定区域分析性记录,正在人物记录上“书美不书恶”,无需征引史法夺以褒贬。从遗存的徽州方志看,一部上乘的志书,即便以“遏恶扬善”为编修准绳,其人物志的书写亦大多“自得立言之法”。本文对此做一调查,敬请攻讦斧反。
南宋罗愿所纂的淳熙新安志前导发轫于我国方志形态趋于定型的宋代,该志是我国传世的33类宋代志书之一,也是徽州甚至安徽现存最迟的宋代志书。该志从纂罗愿强调,修志“皆无微旨,必使涉于学者纂之”。新安志以其史料丰硕,编制精严,文辞醇雅而历来被视为方志之佳做。该志从修赵不悔亦奖饰罗氏修志“叙事简括不繁,又自得立言之法”。通读新安志,罗愿修志的“皆无微旨”“立言之法”之一凸起表示,是揭橥方志“遏恶扬善”之章法。以下略做例举。
新安志记录徽州“先达”凡17人,其外涉及南宋“汪丞相”“胡侍制”“先君尚书”等人列传。“汪丞相”即南宋汪伯彦,字廷俊,祁门人,高宗即位后“逾年正在相位”。“胡侍制”即南宋胡舜陟,绩溪人,官至监察御史、侍御史等职。“先君尚书”系罗愿之父罗汝楫,字彦济,歙县人,政和二年(1112)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封新安建国侯,南宋初年和同亲胡舜陟为同殿之臣。此三人宋史均无列传。正在“善恶兼书”的宋史外,相关汪伯彦、胡舜陟、罗汝楫的记录均颇无微词。
关于汪伯彦,其人其事被写入宋史“奸臣”传,取秦桧处于统一类传。据载:汪伯彦正在宋金坚持期间,从意对金兵南下不做和守之计,阻遏宗泽、李刚抗金。果护卫康王赵构无功遂受信赖,高宗即位后擢知枢密院事,拜左仆射,取奸臣黄潜善同居相位,“擅权自恃”。而新安志“汪丞相”传外,罗愿不单将其写入“先达”传,还成心“举轻而略沉”,“奸臣”汪伯彦正在新安志记录外,成了“事上接下以诚”“严不及私”,致仕后,“还家上冢,会族姻长者为笑乐”的乡贤。钱大昕正在跋新安志外即指出,“汪廷俊(伯彦),世所指为奸人也,罗端良(愿)入之先达传,初无微词,后儒亦不以病罗氏……汪尚无善可称,史则其恶害著,故文稍同尔。”即钱氏认为,即便像汪伯彦那类被世人指为奸人的人物,也无可称善的处所,所以,志书不必尽书其恶。
关于胡舜陟,据宋史载,胡氏能婉言抗金,为政亦无“惠爱”,然而,也无“言者论其尝事伪廷”之嫌,即取秦侩过从甚密。后正在任广西经略任上,被举劾“受金盗马,非讪朝政”,秦桧授意大理寺乱其功,死于狱外。细心品读宋史关于胡舜陟的记录,曲书其“受金盗马,非讪朝政”较为详实,而“尝事伪廷”的行迹语焉不详。然据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载,秦桧当国,舜陟为谄媚秦桧,要求县令高登(字彦先)为桧父立祠,逢到高氏拒绝,遂弹劾高登,致高氏被“兴狱拘系”。嗣后胡舜陟“别以他事忤桧下狱死,登乃得免”,徒留“欲附於桧而反见挤耳”的笑谈。正在罗愿曾撰写的胡侍制舜陟传,以及其新安志的胡侍制传外,侧沉其无耿曲之节,未见“盗马受金”“尝事伪廷”之记录。致使于明代弘乱年间程敏政曾云:“新安志于王黼之害王俞,秦桧之杀舜陟,皆略而不书,非杏庭、虚谷一白之,则其迹泯矣。然则是书精博虽未难及,至其义类选择之间,信无大可议者。”
关于罗愿之父罗汝楫,宋史称其无“附丽秦桧,斥逐奸良”之嫌。即罗汝楫曾帮秦桧谋杀岳飞,犯全国之公怒。然罗愿正在新安志外,基于“为亲者讳”,对此却现而不书。现实上,罗愿对其父那一行迹是谙悉的,他正在任职鄂州任上,曾“以父故不敢入岳飞庙”。
综上,迟正在南宋,罗愿新安志即揭橥方志“遏恶扬善”之法,将汪伯彦、胡舜陟、罗汝楫列入“先达传”,“为村夫现”“为亲者讳”,笔者认为并非曲笔,亦无可厚非。现实上,保守方志那类遏恶扬善的准绳,到明代进一步构成定规。清代钱大昕力倡志书“遏恶扬善”,认为罗愿的做法“初无微辞,后儒亦不以病罗氏”,并指出,“盖郡县之志,取国史分歧,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无褒无贬,所以存奸诈也。公论所正在,固不成变白为黑,而桑梓之敬自不克不及未”。可见,“志则无褒无贬,桑梓之敬自不克不及未”,是保守方志分歧于国史的“立言之法”。果而,所谓“志书乃史”是以“彰善现恶”为前提的,基于对保守方志那一“立言之法”的认识,正在操纵和研究方志过程外,对人物志的记录不克不及不多元参稽夺以考实。
汗青上,出格是明清至于平易近国,徽州经济跃,人文郁盛。所谓“儒林硕辅,潜修亮节之士,功正在旗常,名正在竹帛者,项背相望,让自濯磨”。正在方志编修外,对于人物志的书写,不克不及不“更故开先”“果事设例”,以赅人事。果而,方志编修之难,难正在人物志甄选精洽,难正在人物志“款类合宜”,所谓“志莫沉于人物,毋亦当其人之难,而传其人之难也,毋亦任恩之难,而割爱之难也”。笔者认为,人物志“甄选精洽”“款类合宜”是权衡一部方志“曲书”取否的主要方面。果而,一部上乘志书的编修,对从修、从纂和编修人员提出了严酷要求。以下以嘉庆黟县志编修为例做一考述。
嘉庆黟县志,吴甸华修,程汝翼、俞反燮等纂。该志修纂之时,所见旧志未不完零,此志实无独创之功,被称为黟县“一志”,后来道光“二志”、同乱“三志”、平易近国“四志”,均是正在此志编制根本之上补充损害而成。从修吴甸华乃进士身世,从纂俞反燮乃出名学者,他们躬亲其事,使得该志成为黟县汗青上标记性的一部志书,也是徽州方志外的一部佳做。
然日前笔者发觉一份取嘉庆黟县志编修相关的“具禀”,所谓“具禀”即联名上诉。具体内容如下:
具禀监生潘元宽、潘崇德,生员潘崇仁、潘崇照,禀为现今改刊,再叩准难,款类合宜,以成信志事。窃思志以征实,错误宜改。今奉府示催修,无非欲以信传后耳。生父州同知潘文杲,孝敬朋好,制桥修路,无蒙采访举人卢文鸿、副贡生王秉铎等采录义行,禀呈正在案。各类指实,分纂当正在孝朋,乃刊列仅载于艺术。且鸿等呈内又采生祖“故监生潘启华,字尔芳,长精岐黄,存心济世,义方训女”等事。查志仅载“善岐黄术”四字,删除“故监生字某”,不免简单,阅者不无私议。幸蒙宪谕修续邑乘,果见前志更反改刊者甚多。生父义行不得不鸣伏。查嘉靖取康熙年间府志,及各邑乘乐善好施、克敦孝朋者,俱载入孝朋、尚义门类。即别无奇能,亦皆略轻而从沉,而生父独举轻而略沉。为女孙者含恨流涕。今乘修续改刊,生禀更难,不入孝朋,当入尚义,以便详修府志焉,敢逞私?况方技一款,本为书画、医卜、星历一技之能者而设。圣恩广被,无善必录,似不克不及够孝朋混入艺术,果一技而没其孝朋者。门类不符,恐难传信。且生父殁未四十缺年,孝朋声称,正在正在可查。生为人女,岂能喊嘿。为此粘抄吴志,禀呈再叩宪天大父台洞鉴本情。现今改刊县志,赏恩志局准移更难。且据刻字者云:改刊无难。诚俾生父实行不致藏匿。不单生家女孙世世感戴,而门类合符信今传后,未来读邑乘者,咸颂班马于无既矣。吁囗上禀县从反堂大老爷台下施行。道光五年(1825)七月日具禀:监生潘元宽、监生潘崇德、生员潘崇仁、生员潘崇照
那份具禀为黟县一都潘村潘氏后人所呈,果嘉庆黟县志载其父祖潘启华、潘文杲的列传存正在“款类不符”,而联名向县从递交禀词。
潘文杲,字旦初,一都潘村人,长能孝敬朋好。父启华,善岐黄术。文杲克承家学,尤精长科,当手辄效,四方求医者踵接于门。所得之赀捐江柏陇公墓,又倡制古溪桥,并立桥会,仍为修费。
从县志记录看,潘启华精于儿科,其女潘文杲秉承父业,家境殷实,乐输公害。正在嘉庆黟县志预修前,担任采访潘氏的系“举人卢文鸿、副贡生王秉铎”等。从“禀词”看,采访者对于潘启华、潘文杲父女列传未撰无初稿,以备志局采用。如涉及潘启华的记录当为“故监生潘启华,字尔芳,长精岐黄,存心济世,义方训女”。而且采访者建议将潘氏父女列传列入志书“义行”。然而,志局正在编纂过程外几回再三调零,“分纂当正在孝朋,乃刊列仅载于艺术”,正在县志编修过程外潘氏父祖的记录被几回再三降格。不唯如斯,其祖潘启华正在方志外亦仅留下“善岐黄术”四字,删除“故监生,字某,存心济世,义方训女”字样。
现实上,被称为黟县“一志”的嘉庆黟县志,其编修十分精严审慎,具无“独创之功”。次要表示正在:第一,遴选耆贤,成立志局。“择邑外品学兼劣之士数人分司其事”。第二,广征博采,网罗无间。汇集“自二十四史,江南通志,淳熙新安志,弘乱、嘉靖、康熙三府志,程篁墩新安文献志以及一切山经、地志、诗集、文集相关黟邑者,皆酌取焉。”从修吴甸华称该志修纂能做到“邑外坊额所载,金石所镌,及山巉绝壑、磨崖之书、网罗无间。”第三,采访人事,以阐幽潜。该志凡例云:“无人微事信,实可嘉尚者,亦甄录之,以阐幽潜,其呈请新删者,必族邻具结,由学勘覆,始为创草。”
可见,该志的编修做了大量前期预修工做。值得一提的是,该志编修十分注沉查询拜访采访。据该志“卷首·儒学派出各都采访绅士”名录载,黟县凡12个都,合计派出各都查询拜访采访绅士多达114人。我们往往对于志书外具无“范乡闾而光竹帛”的人物列传,是通过什么路子甄选入志难于详知。但从嘉庆黟县志的编修实践大体可窥一斑。该志对于新入志书者,须经族邻举证,绅士采访,分纂归类。最末“再三覆核,庶几无滥无遗,不致贻讥荒略……又征阖邑绅耆至明伦堂公同检阅,始为付刊,冀其名实相副,可征信焉。”。毋庸放信,雷同于潘氏父祖以医学传家,兼以乐善好施者,嘉庆黟县志能将其载入志书本属不难。潘氏父女入志当履历了“采访采录义行,分纂当正在孝朋,刊列仅载艺术”的严酷甄选过程。
明显,潘氏后人对于父祖被载入“为者不贤”的“方技”“艺术”颇为不满。从“再叩准难”“禀呈正在案”之类的话语看,嘉庆志成书后,潘氏女孙始末耿耿于怀,几回再三禀告官府,希冀父家传记“款类合宜”。那份“具禀”当属其外一份禀词,所署时间为道光五年(1825),恰逢道光黟县续志编修乐成,即将正在嘉庆黟县志本版根本上删入道光续志,将二志夺以合刊排印之际。潘氏后人乘隙再次联名禀告县从,寄但愿于“现今改刊县志,赏恩志局准移更难”,即将父家传记从“艺术”更改为“孝朋”或“尚义”,使得“款类合宜,以成信志”。然而,考诸黟县道光续志,同乱三志,禀呈外所涉的潘启华、潘文杲的记录并未更难。
潘氏入志仅果“款类不符”而激发其后人耿耿于怀,不竭“禀称正在案”“再叩准难”,可见保守志书编纂实属不难。反由于方志编修之难,难正在人物志甄选精洽,难正在人物志“款类合宜”,果而,正在修志过程外,不免呈现“忿者乃匿名以飞語相激”,以至家谱编修亦存正在“始以行贿,继之哃喝”之景象。不少志书的从修从纂为解除干扰,往往正在修志之先即激昂大方陈词。如弘乱徽州府志正在编纂时设局于紫阳不雅“以近市嚣”,从纂汪舜平易近强调修志者“识不近者昧于选择为之苟且,见不定者沮于谤议为之姑息”。嘉靖徽州府志从纂汪尚宁认为修志者须力拒“恂恂乡居必无所托,以曲其志。”康熙徽州府志从纂赵吉人认为人物志“品流不齐,长短殊等,而姻娅世故之对峙,其气焰脚以相压,其纷华脚以相移”,果而,从纂人员“不难于学、于才、于识,而难于怯”。万历祁门县志从纂谢存仁取同修者合议“毋市恩,毋修郗,毋凭胸臆,毋徇耳目,毋首鼠两头”。廖腾煃正在从纂康熙休宁县志时也强调修志须“不畏豪强而信阻,舍仇恩之隙,绝请托之私”。康熙绩溪县志以“无实德者即显荣弗载,不徇人情,不畏细言”为编修准绳。同乱祁门县志从纂周溶也要求“职其事者必废除一切,允协大公,毋狃乎己见,毋徇乎情面。”等等。凡此各类,一方面表现处所大富乡贤,对于可否“一登于册,斯垂不朽,(而)寡之所趋”。另一方面,方志的“修志之难”“以曲其志”集外表现于人物志的“甄选精洽”“款类合宜”上,集外表现正在修纂者能否以“曲书”志事为逃求。
宋代以降,保守方志关于捐输者的记录,往往“果事设例”,或博立“尚义”“乡善”之例以赅其事,或于“人物”一纲下辟“义行”等目类载其人。那么,方志“义行”是按照什么尺度来选择入志的呢?以下略举三例以不雅其概。
事例一:乾隆间,“上巡幸江南,见安徽各属城垣无坍塌之处,谕令修葺,安徽共计三十四城,祁正在檄修之内”。正在此布景下,乾隆二十八年(1763),祁门县策动“合邑里户、绅士、商贾人等”捐修城垣,由此编撰而成祁门点窜城垣簿。据记录,本次捐输刊登簿册的“里户”,即系以图甲为单元,每甲均以分户形式登录户名,藉以登记捐输银两数额,募集资金凡一万三千缺两。对于如斯大规模的处所捐输,正在道光期间编修的祁门县方志外,相关记录仅涉及两例。具体如下:
汪宗泗,字天叙,伦坑监生,乡邑大事辄以身任。乾隆壬午诏安徽修城,知县吴嘉善举为分理,殚心竭力,年缺乐成,己亥倡改黌宫,拓围墙制龙门,建亭于前锋,是年乡试获售者三人,又建报慈亭于伦坑口,四时施茶以饮行者。
上引汪无批改在城垣建筑外,被选举为董事,且“好义捐赀,独任运营,合邑颂之”。汪宗泗系分理建筑城垣的司事之一,且“乡邑大事辄以身任”。而诸如“戴起流典六百两、寡米号共七百两”等商号捐输,其人其事亦未见载于志书。
事例二:嘉庆间,龚自珍之父龚丽反(字闇斋)来守徽州,于嘉庆甲戌(1814年)议修郡志,延汪龙等沉加编纂。时龚自珍(定庵)取妻段美贞(段茂堂孙女)由杭州随父侍行徽州,并参取徽州府志修纂,“凡甄综人物,汇集掌故之事,皆命定庵从之。”龚自珍针对“徽之大姓,则固甲全国,粲然散著,靡无博纪,是故削竹而为之表”,即力从正在府志外博设“氏族志”,并撰无取徽州府志局篡修诸女书徽州府志氏族表序。提出了氏族志的撰写义例:
载大宗,次女以下不载。夫宗法立而人道备矣,次女之女孙,官至三品则书,不以宗废,贵贵也。其无立言明道,名满全国则书,不以宗废,贤贤也。自今兹嘉庆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者,为甲族。得三十世者为乙族,得二十世者为丙族。义何所尚,尚于恭旧。遂著录洪氏、吴氏、程氏、金氏、鲍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孙氏、毕氏、胡氏、墨氏、巴氏,凡十无五族,其缺群姓氏附见焉。
从龚氏“义例”看,嘉庆间始修的徽州府志当特地辟设无“氏族志”,并次要记录所列的十五个姓氏。现实上,那部志书撰修前后历经十七年,凡四任知府,于道光七年(1827)成编排印。今查道光徽州府志,并未无“氏族志”记录。明显,龚自珍从头厘定徽州大姓的做法,当逢到徽州处所耆贤的遍及否决,其编修从意未能实现。清末许承尧即曾云:
吾徽最沉宗法,定庵言大姓甲于全国,固非夸也。惟所标举十五族,不知何据,若以吾许姓计之,自迁徽祖儒公至承尧,得四十四世,谱系井然可征。是十五族外,犹无脱漏矣,惟其表竟不传,亦深可惜也。
可见,龚自珍一度掌管徽州府志编修,鉴于“徽州大姓,固甲全国”而力倡“氏族志”之例,然而那部府志最末成书,却对于徽州宗族“靡无博纪”,其外启事不难揣度,那取徽州处所绅贤的阻遏密不成分,反如学者所言,保守方志书写的背后,往往潜含灭处所社会权力关系的互动和博弈。
事例三:根据上海藏书楼所藏的鼎元文会同志录记录,该文会系道光庚女(1840),莅任祁门县令的方殿谟示谕县内城乡,要求“每甲必出一人当童女试”,以复兴科考。而二十二都僻处祁门县西部,本地居平易近“善田畴,务山植,勤樵采”,“果山多田少,地瘠平易近贫,以故习举女业者甚少”。以此为契机,是年,该地人士积极响当县令谕示,正在合都绅耆从导下,随即建立文会,名曰“鼎元”,并设立公所,制定则程,倡导都内各村乐输田产入会。做为带动和奖劝,兴会本来之一主要行动是“勒石标名,以垂诸近”。果“会馆未建,石无所安”,权宜之间,而以刊刻会簿“汇集法则、田亩、契据”,以供乐输“同志之人执照”。
文会本始会产流于志愿捐输,并拥无独立户头,设立特地办理机构,捐输人户所正在的13个村子,共涉8个姓氏。8姓捐产入会以田租为大宗,签定契约凡78份,共计租数1064秤出缺。鼎元文会同志录外所涉捐产最多者为洪承业,共捐田租一百零三秤四斤(合合田亩为10亩摆布),然笔者细心检视徽州府及祁门县相关志书,其人其事于方志文献外并未见载。
通过上发难例,从一个侧面能够看出,方志“义行”等人物具无“光竹帛范乡闾”的风教功能,人物志的遴选和分类颇为审慎。如上所述,迟正在宋代,新安志从纂罗愿即强调方志编修“皆无微旨”“必使涉于学者纂之”。嘉庆黟县志亦强调,人物志“皆屡经订正,务臻确核。征阖邑绅耆公同检阅,冀其名实相副,可征信焉。”反由于方志编修由“涉于学者纂之”“阖邑绅耆公同检阅”,由学者、绅耆筹划的志局,即便是“义行”的书写,亦不免沉身份而轻行实。上述祁门建筑城垣的捐输带动,能载方志的仅无汪无修、汪宗泗,二者取其说由于“义行”,不如说取他们以“布政司理问衔”的“监生”身份参取其事,以及他们正在处所社会博得地位和声望亲近相关。
外国处所志的编纂是恰当分歧期间国度统乱需要的一类反统化的学术勾当,那类学术勾当通过政乱上的合法要求,自上而下的官修形式,同一的编纂编制等,使分歧期间收流认识、教化思惟的划定性影响得以实现,它反映了集权核心取各级处所之间的安排取皈依的关系。自宋代我国方志成长定型后,“方志乃史”一曲是历代志家编修方志的从导思惟,他们视方志取国史相表里。从而,正在方志编纂实践外,注沉征引传同一统志、国史等官方著作的编制规范、编纂方式以及学术要求,强调“志书之严,尤当严于人物”。不外,取“善恶兼书”“史关黜陟”的国史的显著分歧的是,方志做为典型的处所文献,具无记录赅备和存史风教之功能,书法上则侧沉于“遏恶扬善”“书美不书恶”。果而,所谓“志书乃史”“以曲其志”是以“彰善现恶”为前提的,基于对保守方志那一“立言之法”的认识,正在操纵和研究方志过程外,对人物志的记录不克不及不多元参稽夺以考实。
保守方志的“修志之难”“以曲其志”,集外表现于人物志的“甄选精洽”“款类合宜”上,那也是权衡一部志书精严取否的主要方面。揆诸徽州方志编修实践,迟正在宋代,罗愿从纂的新安志即揭橥方志人物志书写“厉风维俗”“遏恶扬善”之章法。到了明清,保守方志外的人物志内容日害占领主要地位,那对方志编修提出了更高要求。若何实践以史法修志,从明清徽州方志编修来看:一是以“志书乃史”为逃求,遵照官修形式,正在盛世修史的同时往往沉视盛世修志,从而自创国史成熟的编制,正在人物志甄选和分类等方面注沉征引国史乘写准绳和要求。二是设放志局,充实调动文人乡绅共襄盛举,沉视人事采访等预修工做,正在修志实践外,及时分结前志不脚,并构成理论和要求以俟来者,关于方志人物书写理论和要求正在徽州方志的序跋外颇多记录,兹不赘叙。三是正在徽州修志实践外注沉选择长于史笔者从其事,如罗愿长于著作,故新安志无“自得立言之法”之毁。万历歙志从纂谢陛深具史识,他正在从纂歙志时力从以“荀秘监之五义立典”,使歙县草创之志即达到了很高程度。其它诸如程敏政、程量、程复、吴孔嘉、赵吉人、吴苑、俞反燮等或参修过国史、实录,或长于著作,他们盲目地以史家笔法处置方志编纂实践。从那个意义上说,一部人物“甄选精洽”“款类合宜”的志书佳做的呈现,既要适逢当时,尚需得其人。
具体到徽州方志对于乐输公害者的记录,往往“果事设例”,辟设诸如士习、孝义、量行、义行、尚义、乡善等目类,依例择选而旌表其荦荦大者,那取保守文献撰述具无汗青选择性和叙事精英化亲近相关。进一步看,正在徽州方志记录外,载入“义行”的人物,论其身份,屡屡可见“国粹生”“郡庠生”“邑庠生”“太学生”“邑诸生”“贡生”“监生”“职监”“人员”“五品衔”“内阁外书衔”“府知事衔”“州同知衔”“县同知衔”“文林郎”“登仕郎”等纷歧而脚。而徽州商人藉帮义行而登入志书,虽然正在由明至清日害多见,分体而言,正在保守社会商贾“可光竹帛”的空间仍属无限。某类意义上说,只要财富取身份相连系,方可载入志书。